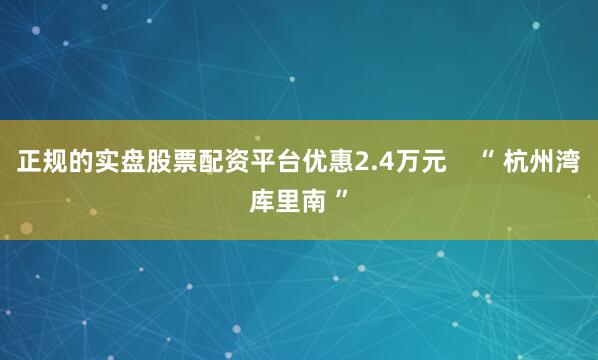自1948年秋至1949年春,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战略决战阶段的众多战役,人民解放军成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辽阔疆土,从而将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解放区紧密连接。此时,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突破358万,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击败国民党军的坚定信念与强大实力。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困境愈发深重,其总兵力锐减至仅剩204万人。其中,可用于直接作战的兵力不过146万余人,而这部分兵力大多数是新近组建或经过重整的。加之这些部队分布在全国从新疆到台湾的广阔土地上,战略层面已无法有效集结和部署,抵抗之势显得力不从心。
驻足南京的蒋介石,此刻仍抱持着一丝渺茫的希望——长江。这条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穿越我国大陆腹地的第一大河,自古以来便被军事家们尊为天然的“天险”,在我国战争史上多次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节点。蒋介石同样期盼在1949年能够重现这一段历史的传奇。
随着1949年元旦的钟声悠扬响起,蒋介石公开发表了元旦文告。尽管他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各方面接连遭受重重挫折,身处逆境的国民党军领袖仍旧决定,以保留其“宪法”和军队为和谈的底线,与共产党展开对话,以期实现“和平”的愿景。
尽管解放军对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抱有坚定信心,但为迅速结束战事、缓解民众之苦,毛泽东同志于1月14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中明确指出,我方愿在“惩处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项和平条款的基础上,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当前,国民党阵营内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由国民党桂系领导人李宗仁接替,担任代总统,并受命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深谋远略的蒋介石始终牢牢掌握军权,即便在宣布“引退”之后,他亦迅速回到奉化溪口故里,紧急召集心腹将领,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总司令。与此同时,他与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白崇禧总司令密切合作,共同筹划江防兵力的部署,积极扩大军力,毫不松懈地备战。
长江之南,国民党军力沿宜昌至上海绵延1800公里的长江防线,部署了115个师的70万大军。其中,汤恩伯所率的主力75个师,约45万人,集结于江西湖口至上海一线,战略重心置于南京以东地区;白崇禧则调集40个师的25万兵力布防于湖口至宜昌一段,意图伺机干扰我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海军力量在长江水域展开了严密部署,共有26艘海防和江防兵舰以及56艘炮艇穿梭巡逻。与此同时,空军也投入了超过300架战斗机,为陆军提供强大的空中支援。
汤恩伯指挥所部精锐兵力向江北要塞及江心洲发起攻势,同时,其主力部队沿南岸展开严密布防,旨在依托已建成的坚固防御体系,借助海空军的强大支援,对人民解放军在江面上的行动实施致命打击。他得意地宣称:“长江立体防线坚不可摧,如非共军能在江面上如履平地,则渡江之举必将无功而返。”
针对国民党一方面寻求和平共存,另一方面却在积极加强长江防线的举措,中共中央军委果断作出决定:我们力主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渡江,但绝不会放松对以战斗形式渡江的全面备战。
二月,肩负着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简称“二野”和“三野”。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军区与华东军区下辖的部队,共计约一百万人,正集结于长江以北,严阵以待,整装待发。
邓小平同志担任渡江战役总前委的书记,与陈毅、刘伯承、粟裕、谭震林等五人一同构成了领导核心。他们秉持中央确定的渡江南进战略方针,同时充分考虑到长江汛期的特殊情形,经慎重决策,决定将渡江作战的时机锁定在3月底。
然而,为与国民党政府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保持高度协同,力求达成一项切实符合人民利益的协议,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放弃3月底发动渡江作战的绝佳时机。因此,渡江作战的时机不得不多次推迟。
3月25日的拂晓,蚌埠孙家圩子村的小祠堂里洋溢着浓厚的热闹气氛。渡江战役总前委正紧急召集高级干部召开会议,共同研讨渡江作战的周密部署。邓小平带着浓重的四川乡音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即将投身于伟大的渡江战役。不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妄图划江自守、苟且偷生,终究不过是黄粱美梦一场!”
邓小平紧握着手中的小木棒,目光如炬地指向墙上的那幅巍峨地图,接着言辞坚定地表述:“我军战略的核心在于充分动员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全部力量,旨在彻底击溃上海、南京、芜湖等区域以及浙赣线上的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或大部分,进而攻克京沪杭地区,并一举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与经济中心。”
现场气氛愈发热烈,陈毅激情澎湃,声音洪亮地宣称:“讲得精彩,长江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我们都必将跨越长江,解放整个中国。同志们,鼓起勇气,奋勇前行,若有人能率先横渡长江,我陈毅将亲自挥毫泼墨,创作一首诗篇以示庆贺。”
谭震林情绪高涨,挥舞着手臂,声音洪亮地宣告:“小平所言,实乃至理名言。无论和谈结果如何,我们都必须勇往直前,横渡长江,挑战那长江天险。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便是整肃军纪,强化武力,为横渡长江做好充分准备!”
会议落幕之际,邓小平同志受总前委之托,着手撰写《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将其呈递军委审批。《纲要》明确指出,二野与三野应联合组建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计划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一线展开渡江作战,继而在向南挺进的过程中,旨在攻占南京、上海、杭州等国民党统治的重镇。
自三月初至四月初,参战部队依次集结于长江北岸,随即投入到渡江作战的筹备工作中。这些来自北方的英勇解放军战士,对水性多有不娴熟,而他们在战斗中渡江,此乃他们首次遭遇此类考验。他们不仅要迅速学会游泳,更需精确掌握潮汐变化、风向走势以及渡江的最佳时机等关键因素。
三月江畔,寒风刺骨,民众们仍身裹厚重的棉袄,而我国解放军战士却毅然抛却棉衣,仅着一身短裤,跃入那冰寒彻骨的江水,刻苦进行游泳训练。那些对水性尚不熟悉的战士们,向老乡借来木梯、大木盆、木板,夜以继日地勤练,反复游弋,终于熟练掌握了水性。
即便战士们不擅长驾驭船只,他们仍诚恳地请求当地船工传授技艺。在内河中,他们刻苦钻研划船、操舟、泅渡以及救护等技能。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长江的水性,部队常在雨夜或是雾气弥漫的时刻,将小船抬至长江中央,挥桨击水,勇破波涛,于江面上排列成战斗队形,进行实战化的演练。
为加强对岸敌情的侦查,我军驻守在巢湖、无为之地的三野第9兵团27军已成立了一支渡江先遣部队。该部队肩负与江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的使命,以便实时获取敌方动态,为后续主力部队的渡江作战提供坚强后盾。
4月6日晚九时,渡江先遣大队的300位勇士分作两队,依次登上船只。左翼的队伍自无为县的鲤鱼套起航,乘坐8艘战舰,勇猛地驶向江南之地;而右翼的队伍则于半小时后,从江心洲的南端扬帆。战士们巧妙地伪装成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并商定一抵达彼岸便立即展开行动,在南陵县的塌里牧村汇合。
在银白的月光映衬下,对岸敌军的碉堡和铁丝网轮廓依稀可辨。就在左路船队驶入江中要道之时,敌军敏锐地察觉了异动,枪声瞬间密集响起。炮弹接连爆炸,掀起的水柱如同小山般矗立,而后又倾泻而下,猛力将船只推向一侧,使其剧烈倾斜。
战士们敏捷地抓起事先准备的木桨与铁锹,挥舞着它们,全力以赴地划动波涛,小船仿佛脱缰的野马,迅猛地朝敌对岸边冲刺,企图强行突破江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三艘速度最快的船只竟然被江心深处预先埋藏的木桩紧紧锁住,无法再前进分毫。
面临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船上的英勇者们毫不犹豫地跃入波涛汹涌的江中,试图强行横渡。汹涌的江流中,漩涡接连不断,无情地吞噬着数位战士的生命,他们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大约在夜幕降临后的十点钟,两支船队相继抵达了登陆地点。在顺利完成抢滩任务后,侦察兵们未稍作休息,他们一边全力抵御敌军江堤阵地的炮火,一边沿着蜿蜒的小径深入到大山之中,寻找掩蔽之地。直至次日拂晓,两支队伍在南陵县的塌里牧村成功实现了汇合。
11日,我方先遣渡江部队勇敢地深入南陵、繁昌、铜陵三县交界的山区。得益于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有力协助以及皖南游击队的并肩作战,我们迅速摸清了敌方江防和换防的详尽情报。随后,我们利用电台将这一关键信息迅速传递回军部。目前,我部已在此地严阵以待,全副武装,随时准备为大军渡江行动提供有力支援。
“老7师回归故里!”
横渡长江,船只自然不可或缺,但江北岸的船舶却悉数被国民党军队拖往江南,或是就地予以破坏。在我军即将发起渡江行动的消息传来后,乡亲们无不激动地表达心声:“我们早已热切期盼这一刻的到来!无论所需何物,尽管直言,人力我们有,船只亦随时待命!”
民众们纷纷将藏于芦苇丛中的渔舟驶离宽阔的河渠,父子同行,兄弟并肩,争相踊跃地报名加入船工行列,与英勇的战士们携手并肩,投身于激昂的渡江演练之中。
尽管生活于斯的人们饱尝艰辛,她们却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支援人民解放军的伟大事业。女人们夜以继日地赶制军鞋,仅用短短两三天,便完成了百余双的缝制。村中住着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奶奶,她心怀战士,便让小孙子搀扶,自己拄着拐杖,来到营地,亲自将一篮散发着诱人香气的锅巴和一罐热气腾腾的茶水,送到战士们手中。
将革命进行到底!
随着春意渐浓,石榴的花朵已悄然绽放。得益于华东和中原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克江北敌军据点,稳固地占据了长江北岸的航道。
在解放军的阵地上,一条条战壕蜿蜒延伸,每门重型火炮都蓄势待发,目光如炬,锁定在长江南岸的目标。突击队员和水手们屏息凝神,蓄积力量,时刻准备投入激烈的战斗。为了避开敌机的侦察与轰炸,战船被茂密的绿色枝叶覆盖,巧妙地隐藏在大堤的掩护之下,寂静无声。
随着解放军紧锣密鼓地部署渡江作战,总前委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电报。电文中明确指出,和谈工作已取得显著进展,和平渡江的几率大幅上升。因此,渡江的具体时间已被调整,推迟至四月末至五月初。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紧握着电报,眉头紧锁。他早已对长江的水文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准确预知4月底至5月初长江的水势将急剧攀升。在此情形下,若和谈未能取得成功,强行渡江的难度将大大增加。而且,百万大军集结在江边,后勤补给的问题也变得尤为棘手。
经周密考虑,总前委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提议在4月20日附近实施渡江作战。中央军委在回复的电文中提到,国共两党已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终修正案)》,并商定于4月20日签署。若国民党政府执意不签署和平协议,则自4月20日起,我们将开始渡江作战,力争一鼓作气,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最终,李宗仁违背了起初的签字承诺,对和平协议投下了反对票。和平谈判的努力就此终结,中共中央军委随即发布了命令,决定在20日夜间发起了渡江战役。消息迅速传遍了长江前线,从指挥官到普通士兵,全军上下都回荡着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奋勇向前,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
4月20日的夜晚,渡江战役的战幕徐徐拉开。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战斗中,由三野的第7、第9兵团协同组成的强大中突击集团,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毅然从芜湖以北的裕溪口至枞阳段的长江岸边发起了英勇的渡江攻势。
在这绵延逾百里的江面上,江水蜿蜒起伏,宛如一条闪烁的银链。随着夜幕的降临,河汊与港湾中藏匿的船队,在月光的掩护下,悄然启航。百船竞发,破浪前行,勇往直前,驶向对岸。
当领航船只与南岸的直线距离约莫三百米时,国民党军队才突然察觉情况,于是匆忙开火,企图进行拦截。一时间,炮弹如暴风骤雨般砸向江面,激起了无数浪花四溅,化作一道道壮丽的浪柱。
早已严阵以待,我军炮兵部队迅速以雷霆万钧之势,对敌方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轰击。国民党军的防线在火光中瞬间被吞噬,夜空被熊熊火焰映照得一片通红。
大约在九点钟的夜晚,第27军的前锋部队在南岸实现了成功登陆,并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第88军的防御线。在这其中,第27军79师253团1营3连5班的战士们,乘坐着木帆船,作为尖兵,最先抵达了南岸,因而被光荣地称为“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依照事先约定的过江信号,登陆的部队迅速点亮了灯火,传递出了胜利的喜讯。
先前挺进敌后的第27军先锋部队,已在山巅与坡地生起了众多篝火,将胜利的捷报传遍大江南北。远眺长江南岸,数十里之内火光闪烁,宛如繁星般闪烁,熠熠生辉。
此刻,国民党坚守的阵地已被熊熊烈焰所吞没,火光映照着江水、白帆,乃至人脸,均染上了血红。无数红旗在火海中随风翻飞,猎猎作响。随着第25军的主力舰队缓缓驶向南岸,敌方的碉堡纷纷喷吐出灼热的火焰,数艘木制帆船不幸葬身火海。
数艘舰艇在猛烈的炮火中遭受重创,弹痕遍布船体,汹涌的江水灌入舱内。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严丝合缝地堵住每一处裂口;尽管桅杆折断,他们依旧拼尽全力划桨,勇往直前;当木制船只不幸倾覆,众勇士纷纷跳入波涛,继续朝着目的地奋勇游去。
勇士们心中忧虑,唯恐枪弹误中船老大,便毅然决然地肩并肩,筑起了一道坚实的人墙,为船老大抵挡住了子弹的侵袭。“冲锋!勇往直前,决不回头!”“登陆即是胜利!”战士们相互鼓舞,勇猛反击岸上的敌人。
第25军的主力部队成功横渡并登陆江南,与此同时,与我军并肩作战的第21军与第24军的船队也陆续抵达彼岸。几支部队顺利实现集结,随即对敌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至21日为止,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即第88军与第20军,在繁昌至铜陵一线的江防阵地,已被中突击集团的大军成功突破。在稳固了滩头阵地的基础上,中突击集团旋即迅猛地向敌军纵深区域发起猛烈攻势。
中突击集团成功击溃国民党军的江防线,一举将千里长江的防线拦腰斩断。江阴地区的汤恩伯将军于21日火速前往芜湖,紧急部署防御策略,并迅速派遣机动部队第99军予以紧急增援。
国民党第99军抵达宣城时,目睹了第20、第88军等部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江防阵地,慌乱之中,不顾一切地弃城南逃。
当汤恩伯在芜湖紧急部署封锁时,21日的19时,我军第三野战军的第八、第十兵团所组成的东线精锐部队,自三江营至张黄港的战线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的第三、第四、第五兵团构成的西线突击集群,在江西彭泽县至安徽贵池县的地带,亦对长江南岸的敌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上游水域有四个不明黑影正迅速向我军逼近!
观测数据揭示,现场共有四艘旗帜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战舰。事实昭示,自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以来,英国军舰“紫云英”号、“黑天鹅”号、“伴侣”号以及“伦敦”号,为彰显大英帝国过往的荣光,擅自展示武力,擅自闯入长江水域。
此刻,四艘英军战舰正逼近江面,炮口一致对准了长江北岸的解放军阵地。在这紧急关头的时刻,特纵炮兵第3团的前哨观察站迅即发出警示信号,坚决要求英军军舰即刻撤出。
英国海军军舰无视警告,肆无忌惮地升起炮口,悍然闯入我解放军的防御地带。紧接着,“咚咚咚”的炮声此起彼伏,炮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猛烈地击中了特纵炮兵第3团的阵地以及附近的修船工人聚集地。霎时,数间民房被熊熊烈火吞噬,众多战士和工人不幸身受重伤。
面对眼前这一幕,特纵炮兵第三团的团长瞬间掷掉军帽,目光如炬地指向敌方舰艇,一声怒吼:“让你们见识我人民解放军的豪勇!”言罢,他果断下达了反击的指令。
刹那间,炮弹如同倾盆大雨般升腾,径直朝那些侵略者飞去。炮声震耳欲聋,响彻宁静的长江上空。烟云翻滚,波涛汹涌,水柱直冲云霄,江面上回荡着不绝于耳的轰鸣之声。
当英舰陷入炮火的围困之中,它顽强地拼搏,将舰上的每一门炮口齐射向江北的解放军阵地,试图逆转战局。我军特纵炮兵第3团奋勇还击,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在炮火与硝烟的交织中,英舰上的“米”字旗已被击打得破碎不堪。
在炮火的猛烈轰击中,英舰“紫云英”号浓烟弥漫,烈焰升腾,船体剧烈颤动,发出令人心悸的悲鸣。昔日“大英帝国”的傲气在这一刻尽失,只能无奈地在桅杆上挂起三面象征投降的白旗。与此同时,其余三艘军舰也纷纷向下游溃散。阵地上的解放军指战员目睹这一壮观景象,纷纷鼓掌欢呼,高声呼喊:“纸老虎的真面目终于揭晓!侵略者开始哀求投降了!”
在炮团坚如磐石的掩护之下,东突击集团下辖的第10兵团,其中第23军部署在右翼,第28军居中协调指挥,而第29军则镇守左翼。三军沿龙稍港至张黄港的战线展开,直指国民党军防御的咽喉之地——江阴地区。
江阴要塞,位于长江下游之畔,依傍着险峻的山岭。山顶之上,炮兵阵地巍然耸立;山腰之中,战壕蜿蜒曲折;山脚之下,地堡星罗棋布。港口处,木桩与铁丝网密布,江面上,舰艇穿梭巡逻,共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壁垒。这一防御体系绵延约20公里,牢牢掌控着东西向的江域,成为国民党在南京东部至关重要的江防要塞。
在关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江阴要塞的地下党组织于22日凌晨3时左右,发动了7000余守军的起义。经过激战,他们成功擒获了要塞司令、国民党军少将戴荣光。起义胜利后,守军迅速调整火炮射击方向,对国民党军的阵地及江面上的舰艇发起了猛烈的炮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了关键的支援。
江阴要塞的起义,令国民党军的江防防线瞬间溃败,极大地催动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节奏。勇猛的第10兵团乘着渡江船只,仅用十分钟便抵达了南岸的国民党军阵地。面对敌军密集炮火的猛烈袭击,勇士们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前赴后继,最终成功抢占了滩头阵地。
在江阴一带,解放军成功突破敌方江防,汤恩伯紧急指挥国民党部队发起反击,企图将解放军围困于滩头阵地,或将其驱逐回长江。战斗异常惨烈,至22日下午,我第10兵团成功击退了国民党部队的多次反扑,并在江南地区构筑起以江阴为核心的正面防线。该防线宽度超过五十公里,纵深达十余公里,且防线仍在不断向更广阔的区域延伸。
在第十兵团的紧密协作下,第八兵团的二十军在22日正午时分顺利解放了扬中。紧随其后,二十六军在22日至23日间成功跨越长江,迅速抵达江南地区。而三十四军则在22日顺利完成了从仪征至扬州段的江面渡江任务,次日便猛攻镇江。与此同时,三十五军于21日攻克了江北浦镇的战略要地。面对即将被全歼的绝望,防守的敌军第二十八军匆忙向南撤退,浦镇与浦口也随即获得解放。
目前,西突击集团已成功越过了从安徽西南部的枞阳镇至望江段的长江天堑,主力部队正沿着浙赣铁路线挺进,此举有效切断了汤恩伯与白崇禧两大集团间的联系。
肩负着支援西突击集团的重要使命,第四野战军的前锋部队与中原军区的部队协同作战,在攻克黄梅、浠水、汉川等地后,继续挺进长江北岸,有效遏制了白崇禧集团的动向,从而确保了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侧翼安全。
至此,解放军已成功突破国民党在长江的防御线,使得国民党军队陷入被分割围剿的危急境地。汤恩伯于22日紧急启动全面撤退计划,下令芜湖以西的部队撤退至浙赣铁路沿线,芜湖以东至常州以西的部队撤退至杭州,而常州以东的部队则需撤退至上海。一时间,各路国民党守军纷纷抢夺逃生之路,场面如同江堤溃决,局势几近失控。
此刻,南京城内弥漫着一片混乱,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纷纷涌向京杭公路。而国民党立法院的225名委员,则先行一步,搭乘飞机逃离了南京。
面对重重困境,国民党代理总统李宗仁显得束手无策。在那个寂静的深夜,他接到了国民党和谈代表章士钊与邵力子的来电,他们向他转达了中共方面的立场,诚挚地邀请他留守南京,并承诺将给予他尊贵的礼遇。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去的决定。
22日,李宗仁搭乘的“追云”号专机缓缓升空。穿梭于南京城的碧空之上,机翼划过两周,此时东方渐露晨曦,长江如同一条盘旋的丝带,城外炮声阵阵,此起彼伏。随着飞机的高度不断攀升,渐渐没入云层,它向着桂林的方向迅速驰骋。
坐落在长江北畔的浦口,第35军政委何克希沿着江堤缓缓前行,目光所及,对岸的下关车站和轮渡码头一览无遗。南京城被苍翠的紫金山和清凉山环抱,脚下长江的波涛翻滚,宛如忠诚的卫士,严密守护着山口城池。这座城市,已然触手可及。
23日正午时分,在浦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废弃宅第之中,第35军军部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何政委向在场的各位庄严宣布:我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已成功横渡波涛汹涌的千里长江,敌军全线陷入瓦解。遵照前线指挥部的指令,我军即刻发起正面攻势,直指南京城!
神圣的使命在每一位同志的心中激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彼此间交换着鼓励的眼神,仿佛在无声地誓言:“同志,南京城,我们定将抵达!”何政委声如洪钟地宣告:“同志们,我们必须分秒必争,迅速制作筏子、打造木排,积极寻求夺取对岸敌人船只的策略,各种手段一应俱全!哪支部队能够率先横渡长江,将那面鲜红的旗帜插上‘总统府’的楼顶,该部队便将赢得荣誉与表彰···”
号令如雷贯耳,战士们满怀斗志,迅速行动,搜寻船只,搜集木材,紧急制作木筏,现场一片热闹非凡。随着夜幕降临,第35军104师的侦察小队乘坐小舢板,勇猛地率先横渡江河。约20分钟后,他们成功带回一艘渡轮,并迅速传回喜讯:南京城内的敌军已溃不成军。

南京下关的工友兄弟们,悄然无声地驾驭着他们心爱的“京电”号汽轮,渡过滚滚长江,助力运送军力。“解放军的战友们,你们的辛勤付出,真是令人敬佩!”“敬爱的工友兄弟们,我们衷心感谢你们的无私援助!”工人们与战士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汇聚成一片激情洋溢的合唱。
江面之上,舟楫往来络绎不绝。105师第35军渡过长江后,便直指南京市中心。曾担负南京城防任务的国民党卫戍部队——暂编第4师,早已弃城而逃。城内仅余散兵游勇与特务分子,他们潜藏于暗处,四处流窜,偶尔还传来几声冷枪。
24日凌晨3时,进入城区的解放军指战员们沿着中山路,如潮水般涌向总统府。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撞开,一名解放军战士登上门楼,扯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将鲜红的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南京解放了!总统府的上空,欢呼声如春雷滚动。
总统府内景象狼藉,文件与纸屑飘散一地,随风起伏。无数双沾满泥土的脚印,踏过十级石阶,涌入二楼总统府的办公室。此时,办公桌上的台历恰好翻至22日,宛如张开双臂,向英勇的战士们宣告:“看,这正是反动王朝的末日!”
24日的拂晓时分,第35军军部所属的车队成功渡过浦江,抵达了下关。下关码头上,迎风飘扬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醒目标语横幅。在中共地下党的精心组织下,工人们与学生们携手合作,共同维持着现场的秩序。当车队缓缓驶入挹江门时,热情的市民们纷纷点燃了鞭炮,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迎接解放军队伍的到来。
南京城内,商户们争相敞开大门,人潮涌动,汇聚成一片欢腾的海洋。店员与市民们携手共庆,齐声向巡逻的解放军战士投以热烈的欢呼;即便是远道而来的外籍侨民,面对威武的解放军战士,亦不禁挥舞手臂,表达出由衷的敬意。
在励志社门口,人民解放军的汽车行列缓缓驻足。随着第35军军部的人员走出车厢,他们立刻被热情洋溢的群众包围。市民们争相递上香烟、糖果等慰劳品,面对解放军婉拒的姿态,他们不禁好奇地发问:“英雄们,为何不接受我们的一片好意呢?!”
励志社,曾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们莅临的场所,而今却摇身一变,成为第35军军部的临时指挥中心。接线员刚完成电话设备的部署,便接连收到各地传来的胜利喜讯。军部参谋牵挂着南京解放的喜讯,迫切希望尽快将这一喜讯传遍全国,遂当机立断,将电话线路直接延伸至新华通讯社。
新华社负责人接到电话,得知南京解放的喜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兴奋地高呼:“太棒了!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这无疑是一则重大新闻,我们将立即进行报道。”电波迅速扩散,南京解放的消息瞬间传遍大江南北。
“旌旗所指,南向大江之滨,滔滔洪水如龙腾空,直冲九霄;勇征金陵,洗去天地尘埃,四海同庆,齐颂人间焕新容。”
黎明之际,邓小平与陈毅在向中央汇报完最新的战况之后,不惧细雨的洗礼,携手漫步于田野之上,共同商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计划。
4月27日,邓小平与陈毅并肩领队,在瑶岗举行了别离的仪式。接着,他们乘车向东进发,当晚便顺利穿越长江,抵达了南京。刘伯承在接到中央军委的指令后,也赶回了南京。邓小平、陈毅、刘伯承三位战友的重逢,喜悦之情溢满心间。那一夜,南京正式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并一致推举刘伯承担任主任之职。
5月1日,南京长江路旁,昔日国民党大会堂的庄重之地,中共中央华东局盛大举办了解放军与地下党干部的胜利会师庆祝活动。刘伯承同志在会上激情满怀地发表演说:“历经长达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南京这座古城终于重获新生。这一天,中国人民翘首以盼的解放时刻终于降临。然而,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路上的第一步。我们应当齐心协力,致力于构建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南京!”
南京的解放,宣告了蒋介石统治时代的落幕。渡江战役的胜利,吹响了决定性阶段的号角。此后,人民解放军的攻势愈发猛烈,三野在郎溪、广德地区成功围歼了南逃的国民党军队,并相继解放了杭州、上海等城市。与此同时,二野切断了浙赣铁路,解放了南昌等地。
截至6月2日,我第三野战军一部已成功解放崇明岛,此举标志着持续42天的渡江战役取得了显著胜利。在此役中,人民解放军共击溃国民党军43万余人,一举破灭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迷梦。
天臣配资-普通人怎么加杠杆买股票-国家允许的配资平台2022-炒股配资炒股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炒股配资网站详解韩国财政部长提名人表示
- 下一篇:配资选股"我们打车回去吧